海菲兹与小提琴
北京中器研究院 2010/7/29 15:02:39 点击:2446次
人们经常问我关于练琴的问题。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并不赞成“整天工作不要玩”这样的理论。假如要我每天练六个小时琴的话,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的。首先,我从来不主张练琴的时间过长……练得太多几乎和练得太少一样不好!其次我还有许多喜欢的事情要去做。我喜欢看书,许多体育活动我也非常喜欢,例如,网球、高尔夫球、骑脚踏车、划船、游泳等等。当我练琴累了的时候,我就拿出照相机到外面去拍几张照片!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摄影迷”了。最近我又有了一部新的汽车,学开车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我从来不相信苦练,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个曲子拉成形,这就说明他正在把这首乐曲判处死刑。
为了能正确地表现音乐,当然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不能使听众感到演奏者正在那些困难的乐句中作挣扎。必须对那些困难的乐句进行更加深入的练习,以便使你能不感到困难地在公众面前演奏。
我每天的练习很少超过三小时,而且星期天通常总是放假的,有时一周中还要多加一天假日。有人说我每天练习六个小时,甚至是七,八个小时,这简直是荒唐,这样练琴我还能活吗!
当然,我说我每天练习三个小时……或是说我没有每天练习七、八小时,你也不能太刻板地去理解。有时当你拿到一首新的乐曲,而这首曲子又非常有趣的话,你就会想多练了,因此,请你不要认为由于我不主张过度的练习,而认定我从来没有多练过。有时琴练得很多,只是由于你想练这么多,而不是不得不练这么多。
但是,就我自己来讲,为了保持良好的演奏状态,我从来没有感到每天需要超过三小时的练习的。
我想,当我演出时,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的容易。所以看上去那么容易,是因为我在上台之前做了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当然,通过艰辛的练习,困难的句子就变得容易了.
对我来讲练习是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首先,我研究这首乐曲,我把这叫做脑力劳动。然后我练习它,我把这叫做体力劳动。我在达到目的地之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请不要忘记,当你花了一定的精力练琴以后,就要休息一下。正如我们做别的事情之后不也要休息一下吗?所以即使我每天练习三个小时,也不是连续练的,而是在三个小时中间有几次休息。
就技巧来说,有人说我的技巧是天生的,因为表面上看来我并不需要刻苦地练习就可以获得这种技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是同样需要训练、巩固和提高的。假如你也象我一样从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使用一把1/4的小琴,我想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小提琴也会变成你的本能了。在我学习小提琴的第一年,我就能演奏所有的七个把位,而且我也能拉开塞(Kayser)的练习曲。但是,这丝毫也不能说明那时我已经是位演奏家了。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父亲,他是位很好的小提琴家,是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纳交响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我第一次演出是在维尔纳帝国音乐学校一间挤满了人群的大厅中,那时我还不满五岁,我演奏的是用钢琴伴奏的《牧歌幻想曲》。后来,当我六岁的时候,也是在一间满是人群的大房间内演奏了门德尔松协奏曲。
我在开这些音乐会时一点也不紧张,事实上,我从未紧张过。当然,有时在开音乐会前,有些事情使我感到不安,有时刚上台时有点不太舒适,这可能是因为没睡好觉;吃的东西不合适,胃不太舒服等原因。这当然不能叫做“舞台紧张”了。
我在维尔纳皇家音乐学校时,学习了每个提琴家都学的东西,我想我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并不特别用功,可是还算努力的。:当我不跟父亲学琴之后,就开始跟达维多维奇·马尔金学习,他是奥尔教授的学生。
当我只有七岁的时候,就在音乐学校毕业了。由于马尔金是奥尔教授的一位学生,所以当我在维尔纳音乐学校毕业以后,他就把我带去拉给奥尔听。我并没有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即被奥尔收为学生。而是稍稍等了一下,才被奥尔收为他的私冬学生。
奥尔是一位非常好的、.无与伦比的好老师。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位教师可以达到他那样的水平。请不要问我他是怎样教学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因为他对待每一个学生的方法各各不同。这可能就是他所以能成为如此伟大的教师的原因吧!我大概跟奥尔学习了六年,我在他的班上上课,也上个别课,后来我上课就不太正规了。我从来不拉任何练习曲或是技术性的作品给这位教授听,只拉那些大东西,协奏曲、奏鸣曲以及一些有特点的小曲子。我经常选择那些我喜爱的东西拉给他听。
奥尔教授是一位非常敏感的、精力非常旺盛的教师,他从来也不满足纯粹的口头讲述。除非他肯定你已经懂了,否则他总是拿起他的琴和弓子向你示范。他在演奏上是非常有才能的。奥尔的学生来找他学琴的时候,在技术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只是来向他学习音乐表现的。但是,各式各样的技巧问题,演奏中那些奥妙的地方,奥尔也和教音乐表现的问题时一样,当必要时他都能拿起琴来做给你看。最有意思的是,学生越是好学,越是有能力,这位教授教给你的东西也越多。他是位非常伟大的教师。
就拿弓法来说吧,真正的运弓技巧是奥尔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记得当我开始到奥尔那里去的时候,他对我所讲的有关运弓的各种问题,是我在维尔纳所从来没学到过的。我很难用语言讲清楚我怎么能把手臂抬得这样高而不使手臂和手腕紧张的,我想你看看我拉琴就会知道了。
但是奥尔教授所教的运弓是很特别的。令人感到运弓的动作越方便、越优美,就越不紧张。
在奥尔的班上通常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个学生。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对自己演奏的批评和纠正。在轮到你演奏前听听别人的演奏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奥尔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我记得我非常喜欢听和我同时上课的优秀的小提琴家波里扬基(Poliakin)和汉森(Cecile Hansen)的演奏。奥尔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严格、要求很高的教师,但他又是位非常有同情心的教师。假如我们演奏中有某些东西不合适的话,他时常会用这采开个有趣而绝无恶意的玩笑,他先说一句客气话,然后说“我想你大约是新换的弓毛吧!”或“这种新的琴弦真叫人恼火!”或“大概又是天气不好吧?是吗?”等等类似的话。
奥尔教授的考试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拉独奏,而且要视奏困难的乐谱。
有些技术我学起来比别人更加困难。我认为我学习连顿弓是很吃力的。当我十多岁第一次学习连顿弓时,的确感到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我的连顿弓非常的不好。后来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演奏维尼亚夫斯基降F小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里面都是连顿弓和双音,当奥尔教授教了我他演奏连顿弓的方法之后,正确演奏连顿弓的方法突然地出现了,我就这样地学会了这种弓法。
对我来讲,掌握小提琴就意味着能把小提琴变成自己驯服的工具,通过演奏者的技巧和智慧使乐器能按演奏者的意愿做出反应,演奏家应该是乐器的主人,乐器是他的仆人!是听话的仆人!!
由于掌握小提琴技巧具有脑力劳动的性质,所以就不能只把它简单的看成是练好某个动作的问题,科学家可能会讲清楚头脑是怎样指挥手指、手臂演奏出无数变化的声音来的。那些甜美悦耳的声音,连弓、八度、颤音、泛音等,都和讲话一样,有着演奏者独有的特点。当一个人练习泛音时,他要耐心地寻求非常纯净的声音,要有良好的音准。他要细心地对待所发出来的声音,试了又试,在指法和弓法方面寻求改进的办法。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地就会了!“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事实上,你心里弄明白了,你就会了,就是这么回事。我非常愿意向音乐界揭示掌握小提琴技巧的全部“秘密”,但是到底有没有可以让那些没入门的人使用的“秘密”呢?假如有位提琴家他的某种技巧比别人好,那么大家就去问他,是用什么“窍门”学会的。但是,事情并不如此,他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个东西。通常,他更多依*的是头脑的能力而不是生理的动作。我并不是想降低教师的作用,他们在音乐家成长的过程中的确起着重大作用;但是你看看同一位著名教师所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学生,他们的跳弓、八度、连弓、颤音是多么不同呀!
要想有效地掌握小提琴技巧,就要细心地研究自己的特点,把思想集中在你所希望演奏出来的音质上面,这样迟早你会找到表现自己的方法的。音乐不是在手指或手肘中的,它是在人的神秘的自我之中,也就是在他的灵魂之中;而他的身体象他的小提琴,只不过是个工具。
当然,伟大的艺术家必需有适合他的工具,取得成功是需要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有特点的提琴家都可以通过他的声音,他的音调为人们所辨认出来,就象我们通过讲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是谁在讲话那么容易。有谁能讲清楚人们的内在感情是怎样和他的手指的颤动协调在一起的呢?我的小提琴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我内心所感受到的声音,这是一种非常有个性的感情。通过纯粹的模仿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只是采用适合别人的方法是永远也取不到最好的效果的。虽然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使用自己的创造性。当然是有一些学习小提琴技巧的标准方法,这些大家都非常熟习,用不到在这里讲了。但是艺术的微妙之处,就是那些把一般的小提琴家和伟大的小提琴家区别开来的东西,这一定是来自演奏者的内在感情而不是外界的影响。你可以造就一个提琴家,但你永远也不可能造就一个艺术家!
评论家很喜欢注意曲目,每个提琴家当然喜欢演奏他们所最喜欢的曲子,每首曲子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每个人最喜欢他最理解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我喜欢演奏古典作品,例如,勃拉姆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门德尔松等等,但是,我在1913年就在莱比锡的格温豪大厅(Gewandhaus),由尼基什(Nikish)指挥下演奏了勃鲁赫g小调协奏曲,他们告诉我,这个乐队所伴奏的独奏家中象我这样的年纪的只有约阿希姆(Joachim)一个人。
还有柴可夫斯基协奏曲,这在1912年也是由尼基什指挥柏林爱乐乐队在柏林演出的,还有勃鲁赫g小调和一些其它作品。1914年由沙富诺夫指挥,我在维也纳演奏了门德尔松协奏曲。1917年我在芝加哥演奏了勃拉姆斯协奏曲,使用的是奥尔所写的极为优秀的华彩乐段。
我认为勃拉姆斯为小提琴所写的协奏曲犹如肖邦为钢琴写的音乐一样,因为这部协奏曲在技术上和音乐上都和其它的小提琴作品不一样。肖邦为钢琴所写的音乐也是如此。勃拉姆斯协奏曲从技术上来讲不见得比帕格尼尼协奏曲难,但是从音乐表现上来讲,肯定更复杂而深刻。
在贝多芬的协奏曲中我感到有一种朴素单纯的美。因此,这使得它比许多技术复杂的乐曲更难于演奏好。每有一点缺点,有一点点不准,就会使这部作品的美受到损害。
除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外,还有一些俄国的协奏曲,例如格拉祖诺夫等人写的协奏曲。我知道是小提琴家金巴利斯特首次来这个国家介绍了这部作品,我打算下个季度演奏它。
我当然不能只是演奏协奏曲,也不能只是演奏巴赫和贝多芬。所以选择曲目是件困难的事。演奏者总是可以陶醉在为此种乐器而作的伟大作品中的,而听众则要求有变化。同时,演奏家也不能只演奏听众所要听的东西,听众要求我每次音乐会都演奏舒柏特的《圣母颂》和贝多芬作的《僧侣的合唱》,但是我却不能每次都演奏它们。我想如果曲目完全由听众去安排的话,那恐怕都是些非常流行的东西。我们也应当想到听众是各式各样的。
我尽力想平衡我的曲目,以便使每位听众都能从我的音乐会中找到某些听得懂的,或是喜爱的作品,我希望在下一个演出年度中准备一些美国作品,这并不仅是为了礼貌,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确是好的,特别是由斯佩丁(Spalding)、布雷(Cecil Burleigh)和格拉斯(Grasse)等人所写的那些小品。
尽管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了音乐,尽管我非常热爱音乐,可我还是认为音乐不能是生活中的唯一内容。假如我全部的生活就是听音乐、想音乐、演奏音乐的话,那实在太可怕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学习、去欣赏。我感到,我对其它的事情知道得越多,学习得越多,我就越是能成为一位更好的艺术家。
(本文标题:海菲兹与小提琴 标签:)
为了能正确地表现音乐,当然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不能使听众感到演奏者正在那些困难的乐句中作挣扎。必须对那些困难的乐句进行更加深入的练习,以便使你能不感到困难地在公众面前演奏。
我每天的练习很少超过三小时,而且星期天通常总是放假的,有时一周中还要多加一天假日。有人说我每天练习六个小时,甚至是七,八个小时,这简直是荒唐,这样练琴我还能活吗!
当然,我说我每天练习三个小时……或是说我没有每天练习七、八小时,你也不能太刻板地去理解。有时当你拿到一首新的乐曲,而这首曲子又非常有趣的话,你就会想多练了,因此,请你不要认为由于我不主张过度的练习,而认定我从来没有多练过。有时琴练得很多,只是由于你想练这么多,而不是不得不练这么多。
但是,就我自己来讲,为了保持良好的演奏状态,我从来没有感到每天需要超过三小时的练习的。
我想,当我演出时,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的容易。所以看上去那么容易,是因为我在上台之前做了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当然,通过艰辛的练习,困难的句子就变得容易了.
对我来讲练习是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首先,我研究这首乐曲,我把这叫做脑力劳动。然后我练习它,我把这叫做体力劳动。我在达到目的地之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请不要忘记,当你花了一定的精力练琴以后,就要休息一下。正如我们做别的事情之后不也要休息一下吗?所以即使我每天练习三个小时,也不是连续练的,而是在三个小时中间有几次休息。
就技巧来说,有人说我的技巧是天生的,因为表面上看来我并不需要刻苦地练习就可以获得这种技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是同样需要训练、巩固和提高的。假如你也象我一样从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使用一把1/4的小琴,我想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小提琴也会变成你的本能了。在我学习小提琴的第一年,我就能演奏所有的七个把位,而且我也能拉开塞(Kayser)的练习曲。但是,这丝毫也不能说明那时我已经是位演奏家了。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父亲,他是位很好的小提琴家,是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纳交响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我第一次演出是在维尔纳帝国音乐学校一间挤满了人群的大厅中,那时我还不满五岁,我演奏的是用钢琴伴奏的《牧歌幻想曲》。后来,当我六岁的时候,也是在一间满是人群的大房间内演奏了门德尔松协奏曲。
我在开这些音乐会时一点也不紧张,事实上,我从未紧张过。当然,有时在开音乐会前,有些事情使我感到不安,有时刚上台时有点不太舒适,这可能是因为没睡好觉;吃的东西不合适,胃不太舒服等原因。这当然不能叫做“舞台紧张”了。
我在维尔纳皇家音乐学校时,学习了每个提琴家都学的东西,我想我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并不特别用功,可是还算努力的。:当我不跟父亲学琴之后,就开始跟达维多维奇·马尔金学习,他是奥尔教授的学生。
当我只有七岁的时候,就在音乐学校毕业了。由于马尔金是奥尔教授的一位学生,所以当我在维尔纳音乐学校毕业以后,他就把我带去拉给奥尔听。我并没有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即被奥尔收为学生。而是稍稍等了一下,才被奥尔收为他的私冬学生。
奥尔是一位非常好的、.无与伦比的好老师。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位教师可以达到他那样的水平。请不要问我他是怎样教学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因为他对待每一个学生的方法各各不同。这可能就是他所以能成为如此伟大的教师的原因吧!我大概跟奥尔学习了六年,我在他的班上上课,也上个别课,后来我上课就不太正规了。我从来不拉任何练习曲或是技术性的作品给这位教授听,只拉那些大东西,协奏曲、奏鸣曲以及一些有特点的小曲子。我经常选择那些我喜爱的东西拉给他听。
奥尔教授是一位非常敏感的、精力非常旺盛的教师,他从来也不满足纯粹的口头讲述。除非他肯定你已经懂了,否则他总是拿起他的琴和弓子向你示范。他在演奏上是非常有才能的。奥尔的学生来找他学琴的时候,在技术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只是来向他学习音乐表现的。但是,各式各样的技巧问题,演奏中那些奥妙的地方,奥尔也和教音乐表现的问题时一样,当必要时他都能拿起琴来做给你看。最有意思的是,学生越是好学,越是有能力,这位教授教给你的东西也越多。他是位非常伟大的教师。
就拿弓法来说吧,真正的运弓技巧是奥尔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记得当我开始到奥尔那里去的时候,他对我所讲的有关运弓的各种问题,是我在维尔纳所从来没学到过的。我很难用语言讲清楚我怎么能把手臂抬得这样高而不使手臂和手腕紧张的,我想你看看我拉琴就会知道了。
但是奥尔教授所教的运弓是很特别的。令人感到运弓的动作越方便、越优美,就越不紧张。
在奥尔的班上通常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个学生。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对自己演奏的批评和纠正。在轮到你演奏前听听别人的演奏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奥尔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我记得我非常喜欢听和我同时上课的优秀的小提琴家波里扬基(Poliakin)和汉森(Cecile Hansen)的演奏。奥尔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严格、要求很高的教师,但他又是位非常有同情心的教师。假如我们演奏中有某些东西不合适的话,他时常会用这采开个有趣而绝无恶意的玩笑,他先说一句客气话,然后说“我想你大约是新换的弓毛吧!”或“这种新的琴弦真叫人恼火!”或“大概又是天气不好吧?是吗?”等等类似的话。
奥尔教授的考试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拉独奏,而且要视奏困难的乐谱。
有些技术我学起来比别人更加困难。我认为我学习连顿弓是很吃力的。当我十多岁第一次学习连顿弓时,的确感到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我的连顿弓非常的不好。后来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演奏维尼亚夫斯基降F小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里面都是连顿弓和双音,当奥尔教授教了我他演奏连顿弓的方法之后,正确演奏连顿弓的方法突然地出现了,我就这样地学会了这种弓法。
对我来讲,掌握小提琴就意味着能把小提琴变成自己驯服的工具,通过演奏者的技巧和智慧使乐器能按演奏者的意愿做出反应,演奏家应该是乐器的主人,乐器是他的仆人!是听话的仆人!!
由于掌握小提琴技巧具有脑力劳动的性质,所以就不能只把它简单的看成是练好某个动作的问题,科学家可能会讲清楚头脑是怎样指挥手指、手臂演奏出无数变化的声音来的。那些甜美悦耳的声音,连弓、八度、颤音、泛音等,都和讲话一样,有着演奏者独有的特点。当一个人练习泛音时,他要耐心地寻求非常纯净的声音,要有良好的音准。他要细心地对待所发出来的声音,试了又试,在指法和弓法方面寻求改进的办法。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地就会了!“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事实上,你心里弄明白了,你就会了,就是这么回事。我非常愿意向音乐界揭示掌握小提琴技巧的全部“秘密”,但是到底有没有可以让那些没入门的人使用的“秘密”呢?假如有位提琴家他的某种技巧比别人好,那么大家就去问他,是用什么“窍门”学会的。但是,事情并不如此,他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个东西。通常,他更多依*的是头脑的能力而不是生理的动作。我并不是想降低教师的作用,他们在音乐家成长的过程中的确起着重大作用;但是你看看同一位著名教师所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学生,他们的跳弓、八度、连弓、颤音是多么不同呀!
要想有效地掌握小提琴技巧,就要细心地研究自己的特点,把思想集中在你所希望演奏出来的音质上面,这样迟早你会找到表现自己的方法的。音乐不是在手指或手肘中的,它是在人的神秘的自我之中,也就是在他的灵魂之中;而他的身体象他的小提琴,只不过是个工具。
当然,伟大的艺术家必需有适合他的工具,取得成功是需要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有特点的提琴家都可以通过他的声音,他的音调为人们所辨认出来,就象我们通过讲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是谁在讲话那么容易。有谁能讲清楚人们的内在感情是怎样和他的手指的颤动协调在一起的呢?我的小提琴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我内心所感受到的声音,这是一种非常有个性的感情。通过纯粹的模仿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只是采用适合别人的方法是永远也取不到最好的效果的。虽然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使用自己的创造性。当然是有一些学习小提琴技巧的标准方法,这些大家都非常熟习,用不到在这里讲了。但是艺术的微妙之处,就是那些把一般的小提琴家和伟大的小提琴家区别开来的东西,这一定是来自演奏者的内在感情而不是外界的影响。你可以造就一个提琴家,但你永远也不可能造就一个艺术家!
评论家很喜欢注意曲目,每个提琴家当然喜欢演奏他们所最喜欢的曲子,每首曲子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每个人最喜欢他最理解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我喜欢演奏古典作品,例如,勃拉姆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门德尔松等等,但是,我在1913年就在莱比锡的格温豪大厅(Gewandhaus),由尼基什(Nikish)指挥下演奏了勃鲁赫g小调协奏曲,他们告诉我,这个乐队所伴奏的独奏家中象我这样的年纪的只有约阿希姆(Joachim)一个人。
还有柴可夫斯基协奏曲,这在1912年也是由尼基什指挥柏林爱乐乐队在柏林演出的,还有勃鲁赫g小调和一些其它作品。1914年由沙富诺夫指挥,我在维也纳演奏了门德尔松协奏曲。1917年我在芝加哥演奏了勃拉姆斯协奏曲,使用的是奥尔所写的极为优秀的华彩乐段。
我认为勃拉姆斯为小提琴所写的协奏曲犹如肖邦为钢琴写的音乐一样,因为这部协奏曲在技术上和音乐上都和其它的小提琴作品不一样。肖邦为钢琴所写的音乐也是如此。勃拉姆斯协奏曲从技术上来讲不见得比帕格尼尼协奏曲难,但是从音乐表现上来讲,肯定更复杂而深刻。
在贝多芬的协奏曲中我感到有一种朴素单纯的美。因此,这使得它比许多技术复杂的乐曲更难于演奏好。每有一点缺点,有一点点不准,就会使这部作品的美受到损害。
除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外,还有一些俄国的协奏曲,例如格拉祖诺夫等人写的协奏曲。我知道是小提琴家金巴利斯特首次来这个国家介绍了这部作品,我打算下个季度演奏它。
我当然不能只是演奏协奏曲,也不能只是演奏巴赫和贝多芬。所以选择曲目是件困难的事。演奏者总是可以陶醉在为此种乐器而作的伟大作品中的,而听众则要求有变化。同时,演奏家也不能只演奏听众所要听的东西,听众要求我每次音乐会都演奏舒柏特的《圣母颂》和贝多芬作的《僧侣的合唱》,但是我却不能每次都演奏它们。我想如果曲目完全由听众去安排的话,那恐怕都是些非常流行的东西。我们也应当想到听众是各式各样的。
我尽力想平衡我的曲目,以便使每位听众都能从我的音乐会中找到某些听得懂的,或是喜爱的作品,我希望在下一个演出年度中准备一些美国作品,这并不仅是为了礼貌,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确是好的,特别是由斯佩丁(Spalding)、布雷(Cecil Burleigh)和格拉斯(Grasse)等人所写的那些小品。
尽管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了音乐,尽管我非常热爱音乐,可我还是认为音乐不能是生活中的唯一内容。假如我全部的生活就是听音乐、想音乐、演奏音乐的话,那实在太可怕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学习、去欣赏。我感到,我对其它的事情知道得越多,学习得越多,我就越是能成为一位更好的艺术家。
(本文标题:海菲兹与小提琴 标签:)
- ·北京瑞德提琴制作中心
- ·江苏扬州金陵乐器有限公司
- ·吉林天韵乐器有限公司
-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 ·天津鹦鹉乐器有限公司
- ·苏州民族乐器厂
- ·天津英昌乐器有限公司
- ·河北金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 ·扬州市琼花民族乐器有限公司
- ·上海莱曼钢琴有限公司
- ·杭州余杭西湖笛声厂
- ·上海民族乐器厂
企业会员推荐
- 2015/4/13·钢琴的保养和使用年限
- 2015/4/13·钢琴为什么要有售前服务
- 2015/4/13·为什么要进行钢琴定期的调律维护
- 2015/4/13·钢琴调律对钢琴保养很重要
- 2015/4/13·钢琴的放置,搬运,使用知识
- 2015/4/13·钢琴]钢琴在冬季如何保养呢?
- 2015/4/13·立式钢琴的常见问题与维修方法
- 2015/4/13·数码钢琴的保养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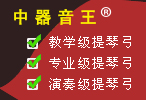








 热点视频推荐
热点视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