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斯倾吐的记忆
北京中器研究院 2013/6/3 14:54:24 点击:3317次
冬夜,细雨,从街头走到街尾,是谁在吹奏萨克斯管。这是一支名曲:《记忆》。我第一次听它,是她离开小巷去海南的日子。
萨克斯倾吐的记忆,如一位盲者,总也走不出烟雨蒙蒙的雨巷。雨巷,没有人影。
吹奏萨克斯管的人,你难道有什么无法倾诉的尘缘,才用这微妙的声音呼唤?而这些飘散如风的音符又被雨水淋湿坠落下来,让人如此苍白憔悴荒凉。我呢?枉为诗人,真情到达顶峰,竟没有言语,惟有泪水结晶为药。
走了,悄然地走了,正如她来的时候,只给我留一丝淡淡微笑。
是的,我们都不相信,我们就居住在同一街巷,经常见着,就是彼此不知姓名,白白地寻问了几年。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新华书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第一部诗集《水果与刀》在《花溪》月刊诗歌编辑西篱君的帮助下,由一位熟人放在书店诗歌类书架上,听说几天下来,没卖出去一本,于是,沉不住气的我,去书店看看。
这天,我等了好久,翻看诗集的读者有,但都是翻翻又放回原处。我几乎有了撤架收书的想法。想必是我的失望让上帝有了些许怜悯,选定她来给我安慰。我在她付款后,跟着她出了店门。她上车,我上车;她下车,我下车;她走快,我走快;她走慢,我走慢……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跟着进了我们居住的小巷,她停住,“你跟我半天,想干什么?”我一时失语,但最终还是表明了用意。说:你手里拿着的,是我的处女集,你是第一个买我诗集的人,我想在集子上留几个字?她捧着书,比我还激动,手抖动着递予我,说:“我可找着你了,蒋德明。”
她说:“读你的诗、散文,有些年了。你的文字,总让人淡淡的忧郁,想哭,又找不出该哭的理由。”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经她提示,隐隐想得起她的一些与我同期刊发的诗句。她说:“曾经好几次想过,在这人来人往的巷子中,会有与你的擦肩而过,却今生不知。不想,会有这样的趣事。”
这以后,我们经常一道谈诗谈人生谈物价上涨甚至谈算命。其实,大多时间是她静静地望着我,听我高谈阔论。而我,在她面前,总有瀑布一般的激情,经常忘了接儿子或答应妻子回家帮忙做饭。
妻子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上她那里找我,从来到去,都是微笑着,而一到家,又总是背对着我。我至今在想,我当时为什么不研究明白,那背对着我的脸,是否还有笑容。
在我们认识后不久的一天,我去还她《美国现代诗选》,她不在,门虚开着,我走进去,在书桌边坐下,书桌上翻开的日记,我看到我名字下边有这么一段话:“冬夜飘浮的红烛中/握住你的名字取暖/是我一生的选择”,我一阵心热,放下诗选走出房门。回到家,这一夜我没能入睡。身边的妻子,刚满周岁的儿子,儿子是可爱的,妻子呢,真找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惟一的不是:她越来越读不懂我写的东西。但见我几日不动笔时,她又总予我以鼓励。
第二天有个出差任务,我走了。出差回来后,我们一下子生疏了许多。这样过了几个月,她说她要结婚了。我虽然惊讶,但还是去参加了婚礼。在婚礼的那晚,妻子让我大吃一惊,她竟是新婚夫妇的媒人!我问妻子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告知一丁点儿?她笑:“发挥你的想象呗。”
婚后,她与丈夫去了海南。临走的头一天,听说她烧了一些日记和诗稿,去了一趟父母的坟前添了几把土。第二天我和妻子送行,也是一个雨天,只是那是春雨,两把伞,四个人。我们慢慢地走着,走着,走到街巷中忽有萨克斯呜呜的声响,她停了下来,我们也都停了下来,寻望萨克斯声响来于哪间屋?良久,她才问我:“你知道这支曲子吗?”我望着她的眼神,有些湿润。她说:“这是一支名曲,叫《记忆》。”
从那以后,我记住了这支曲子。也许是我与吹萨克斯管的人不投缘,越是想听他的萨克斯风,越是一次次空等。今天,真是一个意外。
萨克斯倾吐的《记忆》已经终止。而冬雨仍然飘洒着。清冷的石街有人走动的声响。借着微弱的路灯,望见是我的妻子,她举着雨伞朝我走来……
(本文标题:萨克斯倾吐的记忆 标签:)
萨克斯倾吐的记忆,如一位盲者,总也走不出烟雨蒙蒙的雨巷。雨巷,没有人影。
吹奏萨克斯管的人,你难道有什么无法倾诉的尘缘,才用这微妙的声音呼唤?而这些飘散如风的音符又被雨水淋湿坠落下来,让人如此苍白憔悴荒凉。我呢?枉为诗人,真情到达顶峰,竟没有言语,惟有泪水结晶为药。
走了,悄然地走了,正如她来的时候,只给我留一丝淡淡微笑。
是的,我们都不相信,我们就居住在同一街巷,经常见着,就是彼此不知姓名,白白地寻问了几年。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新华书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第一部诗集《水果与刀》在《花溪》月刊诗歌编辑西篱君的帮助下,由一位熟人放在书店诗歌类书架上,听说几天下来,没卖出去一本,于是,沉不住气的我,去书店看看。
这天,我等了好久,翻看诗集的读者有,但都是翻翻又放回原处。我几乎有了撤架收书的想法。想必是我的失望让上帝有了些许怜悯,选定她来给我安慰。我在她付款后,跟着她出了店门。她上车,我上车;她下车,我下车;她走快,我走快;她走慢,我走慢……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跟着进了我们居住的小巷,她停住,“你跟我半天,想干什么?”我一时失语,但最终还是表明了用意。说:你手里拿着的,是我的处女集,你是第一个买我诗集的人,我想在集子上留几个字?她捧着书,比我还激动,手抖动着递予我,说:“我可找着你了,蒋德明。”
她说:“读你的诗、散文,有些年了。你的文字,总让人淡淡的忧郁,想哭,又找不出该哭的理由。”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经她提示,隐隐想得起她的一些与我同期刊发的诗句。她说:“曾经好几次想过,在这人来人往的巷子中,会有与你的擦肩而过,却今生不知。不想,会有这样的趣事。”
这以后,我们经常一道谈诗谈人生谈物价上涨甚至谈算命。其实,大多时间是她静静地望着我,听我高谈阔论。而我,在她面前,总有瀑布一般的激情,经常忘了接儿子或答应妻子回家帮忙做饭。
妻子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上她那里找我,从来到去,都是微笑着,而一到家,又总是背对着我。我至今在想,我当时为什么不研究明白,那背对着我的脸,是否还有笑容。
在我们认识后不久的一天,我去还她《美国现代诗选》,她不在,门虚开着,我走进去,在书桌边坐下,书桌上翻开的日记,我看到我名字下边有这么一段话:“冬夜飘浮的红烛中/握住你的名字取暖/是我一生的选择”,我一阵心热,放下诗选走出房门。回到家,这一夜我没能入睡。身边的妻子,刚满周岁的儿子,儿子是可爱的,妻子呢,真找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惟一的不是:她越来越读不懂我写的东西。但见我几日不动笔时,她又总予我以鼓励。
第二天有个出差任务,我走了。出差回来后,我们一下子生疏了许多。这样过了几个月,她说她要结婚了。我虽然惊讶,但还是去参加了婚礼。在婚礼的那晚,妻子让我大吃一惊,她竟是新婚夫妇的媒人!我问妻子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告知一丁点儿?她笑:“发挥你的想象呗。”
婚后,她与丈夫去了海南。临走的头一天,听说她烧了一些日记和诗稿,去了一趟父母的坟前添了几把土。第二天我和妻子送行,也是一个雨天,只是那是春雨,两把伞,四个人。我们慢慢地走着,走着,走到街巷中忽有萨克斯呜呜的声响,她停了下来,我们也都停了下来,寻望萨克斯声响来于哪间屋?良久,她才问我:“你知道这支曲子吗?”我望着她的眼神,有些湿润。她说:“这是一支名曲,叫《记忆》。”
从那以后,我记住了这支曲子。也许是我与吹萨克斯管的人不投缘,越是想听他的萨克斯风,越是一次次空等。今天,真是一个意外。
萨克斯倾吐的《记忆》已经终止。而冬雨仍然飘洒着。清冷的石街有人走动的声响。借着微弱的路灯,望见是我的妻子,她举着雨伞朝我走来……
(本文标题:萨克斯倾吐的记忆 标签:)
- ·北京瑞德提琴制作中心
- ·江苏扬州金陵乐器有限公司
- ·吉林天韵乐器有限公司
-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 ·天津鹦鹉乐器有限公司
- ·苏州民族乐器厂
- ·天津英昌乐器有限公司
- ·河北金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 ·扬州市琼花民族乐器有限公司
- ·上海莱曼钢琴有限公司
- ·杭州余杭西湖笛声厂
- ·上海民族乐器厂
企业会员推荐
- 2015/4/13·钢琴的保养和使用年限
- 2015/4/13·钢琴为什么要有售前服务
- 2015/4/13·为什么要进行钢琴定期的调律维护
- 2015/4/13·钢琴调律对钢琴保养很重要
- 2015/4/13·钢琴的放置,搬运,使用知识
- 2015/4/13·钢琴]钢琴在冬季如何保养呢?
- 2015/4/13·立式钢琴的常见问题与维修方法
- 2015/4/13·数码钢琴的保养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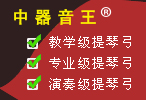








 热点视频推荐
热点视频推荐